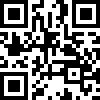为摆摊卖货他们驱车跨越万水千山,困了住二三十元的小旅馆或在车里将就,饿了就用电饭锅下点面条……在实体商业纷纷向线上转型的大潮中,这种远赴千里摆摊模式也成为持续变迁的时代商业中的“活化石”——

2019年的春天比往年暖得更早一些。沙沙安顿好刚刚出院的母亲,便匆忙地与另一个女孩从哈尔滨启程开车奔赴北安一个角落——那是一个百度地图都难找到的地方。如此舟车劳顿,他们目的只有一个:摆地摊。
作为职业赶集人,沙沙的人生不是在摆摊,就是在去摆摊的路上,晚上住二三十一宿的小旅馆或在车里将就,饿了就用随车携带的电饭锅下点面条……在实体商业经历电商浪潮冲击的大时代里,冰城赶集人远赴千里,寻觅电商与店商鲜少触及区,上门“找流量”。对他们来说,这种营生方式是绵延数十载的传承。
在从线下走向线上,
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当下的商业真理。
而“跳线”的赶集人生
成为经济转轨与时代变革中
活体的商业标本,
浓缩着一幕幕谋生的艰辛,
也充彻着精彩与温情的生命故事……

从哈市到三亚千里之外去摆摊“
职业赶集人的赶集之路是一部连续剧。先开到最远的地方,然后把附近方圆百公里内的大集都赶一遍,生意一个集市一个集市地做。
”
家住道里区的孙美华赶集近10个年头,她去过的最远的大集是位于黑河市一个叫罕达汽的小镇,距离哈尔滨近700公里,开车需要8个小时。她要在开集的前一天晚上就赶到。那天凌晨三四点,她来到集市占位置时,已经没有好位置了。
下午1点多,
罕达汽镇大集刚刚落幕,没顾上吃午饭的孙美华就匆忙地踏上了去尖山农场赶集的旅程,两地相距二百多公里,车程3个半小时。到目的地已是傍晚时分,她才吃上中午饭。在她的行程上,尖山大集的下一站是距离这里50多公里的九三农场大集,下一天又是红五月农场大集……
孙美华说,赶集人出来一趟,
天天都得上集,如果误了集
或者没抢到好位置就可能赔钱,
有些大集相隔很远,
时间都是从吃饭睡觉中抢出来的。
与孙美华走一圈就回家不同,80后赶集人沙沙的赶集行程则是循环式的。第一站,驱车3百多公里从哈市到北安、然后是沾河林业局、赵光、五大连池……为了把路费成本摊到最薄,走完一圈后,沙沙再折回北安重启这个循环,直到带去货卖的差不多了才回哈,出去一趟一般都要两三个月。
在我省偏远的乡村和林场大集上,除了坐地商,来自外地的职业赶集人撑起了半壁江山,而漂泊成为他们的共同宿命。哈尔滨的职业赶集人大都是全省到处跑,一些人开车去过西安甚至三亚赶集。
而来哈尔滨赶集的异乡人也不在少数,
其中来自沈阳、长春的最多。
赶集路程远近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其销售产品的消费频次,
卖食品等频次高的活动范围越小,
而卖服装、小家电等则可能全国跑。

“集谱”拿在手千山万水地走
因为行程偏远,
有些大集甚至高德地图上都搜不到。
像自助游事先在网上查攻略一样,
职业赶集人出发前
都会先根据“集谱”做好行程规划。
所谓“集谱”
就是标明全省乃至全国哪个乡镇什么时间有大集的一张纸,赶集人按图索骥,驾车开着导航循踪而至。“集谱”是很多赶集人根据自己赶集经验总结归纳的,市面上买不到,只在赶集人间传递。随着科技的发展,曾经的一张纸现在变成了电子版,通过微信在圈子里传看。
为了省钱,职业赶集人
会住在自己的面包车里
或者找二三十元一宿的小旅馆栖身。
米面、电饭锅、碗筷都是车里的标配,
这样可以简单焖点米饭、下点面条。
如果顿顿都在外面吃,就没有利润可言。
对于赶集人而言,
虽行万里但却没有观赏风景的时间。路过很多名山大川都没机会亲自去爬一下。而对于女人来说,无论曾经多漂亮,一旦踏上赶集这条路就意味着与美丽绝别。长期的风吹日晒,加上睡眠不足,脸上皮肤基本就废了。
“累了想想光头强,饿了想想灰太狼。”
这是沙沙在朋友圈中的自嘲,
也是所有赶集人的生活写照。

千里赶大集VS在家出早市
同样是摆地摊,
赶集人为啥不在城里出早夜市,
而是千里迢迢去赶集?
“现在摆地摊的成本太高了。”出大集之前,沙沙一直在道外一个服装批发市场外出摆地摊,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城里一个3米的摊位一个月要1000元摊位费,平均每米每天11元;而村镇大集面积10米的摊位,每天摊位费二三十元,每米每天不过3毛钱。和沙沙一起赶集的搭档也是一名80后女生,她以前在道里某批发市场出摊,不断上涨的租金让她也成了职业赶集人。
巨大的线下流量,
是驱动赶集人千里奔波的硬核原因。
沙沙有一次在赵光大集上,
一上午卖了五六千元,
近千顶帽子卖没了。
这是在城区早夜市里难以想像的。
“现在城里人人都用手机淘宝,城里早夜市受到冲击不小。”哈市很多职业赶集人除了定期去赶集也在城区出早夜市。他们告诉记者,职业赶集人一般更愿意选择那些偏远的林场、村镇等。因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多是中老年人,他们不习惯甚至不会在网上购物。而且,由于地处偏远,这些地方快递也很不发达,卖东西的店家也有限。所以市场比城里早夜市更大。
为了抢到好地点,很多职业赶集人
一次就交上1年的摊位费。
有时候家里有事,误了集,
这天的摊位费也瞎不了,
因为可以在微信群里
把当天的位置转包给别人。

赶集路上你若不勇敢我替你坚强
职业赶集人的艰辛
绝不止于风餐露宿与披星戴月,
丢货是最让人心痛但却很难避免的。
卖帽子的沙沙经常是
丢了十几顶帽她自己都不知道,
直到有好心的顾客
偷偷暗示她“看好东西”,
她才恍然大悟。
有一次,孙美华去伊春那边出大集,一个女的趁乱偷了她的衣服,被她当场抓到,“我说你把衣服还我,那女的回手就给我一巴掌,血当时就从眉角留了下来。”
正是因为在外讨生活不容易,所以职业赶集人中,夫妻档最多,父子兵也不少。总之,一起走过万水千山、摸爬滚打的都是实在亲戚和过命的朋友。因为赶集路上,你若不勇敢只有同伴可以替你坚强。一个摊子、一车货,遇事一起扛,每天流水不算账,彼此的绝对信任是一起打拼的基石。
另一方面,曾经不认识的陌生人因赶集而成为“铁磁”的在这个行业中特别多。“这是赶集时旁边摊位的朋友送我的,我家还有一把镀金剪刀也是一起赶集的好友送的。”孙美华指着家里的沙发垫说,出门在外,一起风餐露宿的集友很容易成为朋友,你需要啥,在我的摊子里随便拿,我需要啥上你的摊子里随便找,这种相互赠送已经成为赶集人间的一种社交方式,很多赶集人在一个大集上相识后,结伴而行一起去几百公里外赶集是常事。

叫板淘宝赶集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家这个1.8米×1米的沙发垫,在大集上的价格只有10元,而在商场里至少要30元。”孙美华告诉记者,很多职业赶集人都是从厂家直接拿货,没有中间商,所以大集上商品大都很便宜。从价格上看并不比淘宝贵多少,但与淘宝相比,大集上买东西看得见摸得着,这就是电商比不了的优势。比如沙沙卖的棉帽子才5元一顶,这个价格甚至比淘宝上还要低。
现在一两元的商品
在城市的商超几乎绝迹了,
但在省内偏远地区的大集上
仍保留着一元区、两元区的商品:
小木梳、纸篓、抹布、小刀……
品种达百种,
这个连淘宝邮费都合不来价位
正好满足了当地老人消费偏好。
这也是电商冲击下,
大集仍拥有顽强生命力的原因。
早些年,
赶大集的日子甚至成为一些老人计量时间刻度的一种方式。一些地方大集甚至承载着相亲的功能。媒人与男女双方约好大集上见面的位置。双方在假装闲逛中,大量对方身高、相貌,如果印象好便会进一步发展。
逛大集的人以中老年人居多,
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逛为主的休闲解闷族,
另一类是开车来的扫货族。
对于休闲族而言,
即使大集商品价格有些比网上或实体店稍贵,很多小东西,他们还是愿意赶集买,因为赶集已经成为内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而扫货族的特点是大都居住在相对偏远的村镇,买东西不方便,每周或一个月出来一次,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和食品都买回去。一个人一次买走半扇生猪在大集上不是新鲜事。
无论对于哪一类顾客而言,
在偏远的乡村,
赶集买东西都已经成为祖辈
传承下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更像是点缀平淡乡村生活的一种节日。
新闻
札记
赶集人有副业,上“快手”开直播
大集中的商品涵盖了衣食住行,
说大集是线下的淘宝一点不为过。
但与淘宝不同,大集就像一个江湖,
卖各种商品的赶集人
都有自己独门的营销绝活。
比如,有人专门捣蹬“快货”,刚入夏就卖T恤,雾霾来了又卖口罩去了,入冬后又卖热帖了……说白了就是根据当下市场热点进货卖。
除了快货,还有鼓捣江湖货的。所谓卖江湖货,就是通过赶集人的一张嘴加上看似很有信服力的产品试验,把产品推销出去。
卖江湖货的门道是先“圈场子”,就是先吆喝或者演示产品吸引很多人来围观。“圈场子”有点类似于互联网时代苹果、三星的新品发布会。等围观人来多了,能卖多少就要看赶集人的“讲口”如何了。在业内,人们把推销忽悠的套路称之为“讲口”。沙沙曾经遇到过一个卖不粘锅的,“讲口”很厉害,一边煎肉、炒蛋一边白话锅的特征,事毕,锅一点没粘东西,一下子就有很多老头老太太掏钱买了锅。
除了不粘锅,
常见的江湖货还有电动绞肉机、饮水机过滤芯、新型拖把菜刀等,它们的共同特性是非刚需产品,要通过高超的推销和现场演示打动人心刺激购买需求。这类产品由于市场需求量容易饱和,卖江湖货的人经常是全国赶集,其中,最远的从黑龙江一路开车赶集到三亚。
如今,“跳线”的赶集人也玩起了互联网营销。今年沙沙准备把自己赶集的现场拍成视频放在“快手”APP上直播,在微信等线上渠道打开销路。其实像沙沙这样开辟微信线上渠道的年轻赶集人越来越多了,但线下的大集始终是他们的主战场。
当然,大集上也有骗子和托上演的双簧戏。如果遇到价格特别高的名贵中药、保健品、尤其是壮阳类滋补品就要格外小心。骗子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见好就收,别人交了全额的摊位费不卖到大集结束一般不会走,而骗子一旦开张,一两个小时候就收了,一方面他们是暴利赚够了,更重要的是怕被骗者回来找后账。
来源:哈尔滨新闻网
记者:霍亮 文/摄
编辑:马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