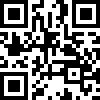在中国戏曲作家中,李渔可说是极为特殊的一位。他生活时代在明末清初,是清代著名的戏曲大师。和其他案头化、文雅化的戏曲不同,而李渔偏偏一反主流,他的戏曲创作更加重视戏曲舞台性、娱乐性的一面。重视戏曲本身特质,强调戏曲娱乐性,何以会成为李渔戏曲创作的主调?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本文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初步的阐释,指出李渔的戏曲创作中沾染了大量的商业性因素,而因为李渔巧妙总结商业规律,才让他的戏剧别开新面,很有吸引力。

一、李渔的人生遭遇及生活心态使得其戏曲创作首要目是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
明清易代鼎革,出处行藏成了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的艰难选择。越是士界名流,所承受的社会以及压力就越大。此种情况下,一些著名文人进行戏曲创作,主要是 “自娱”的性质,用戏曲来排遣郁闷,并借以彰显才情。比如,与李渔有密切交往的吴伟业、尤侗等同样也进行了戏曲创作,却多为自写心怀,借古人之酒杯,浇自身之块垒,曲词典雅,文人味浓厚。
与此相对应,李渔的身份就显得十分尴尬。他没有家学渊源,没有名门重望,其出身甚至可以用寒微来形容。特别是,明末的几次科场失意,表明了他时文创作的乏力,也间接透露出他学问的疏薄。乃至后来李渔绝意仕途,虽有明清易代的顾虑,更主要的应是出于对自身才华的精确分析。他并不适合做一个名流学者似的人物,同样他也没有这样的资本。

生存问题,横亘在李渔面前。他并没有别的技艺,可以换取生存所需。士农工商,他都不在其列。本来还可以学而优则仕,但李渔既已放弃这一道路,最终只剩下了卖文为生——失意文人赖以谋生的最后手段。卖文古已有之,但李渔并不是名家的身份,诗文这等传统文学显然并不适合李渔——显然,出自文坛宗师、名公巨卿之手的诗文更具有价值,至少在商业价值上是如此。于是,小说戏曲的创作,顺理成章的成为李渔首先考虑的对象。事实证明,在挖掘作品的商业价值上,他的确头脑灵活,而且才华横溢。
这里,必须先解释一下明末以来商业文学的发展,至少在表面上是一副欣欣向荣的繁盛局面。随着通俗小说的流行,出版业的发达,不仅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文学交易市场,而且出现了类似近代稿酬制度的某些萌芽。而相对应的是,文士已有自觉的卖文意识。如著名文士归庄就明言:“余亦为沽者之事”。(见《归庄集》卷十《笔耕说》)。文人不但已经把卖文笔耕作为谋生的重要手段,甚至是公然以“沽者”自居无愧色。与以往不同,此期在文人已然有一种 “文章皆为稻粱谋”的普遍心态。
在这样的商业化大潮中,李渔的戏曲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盈利意识。既然别人可以通过卖文谋利,那么李渔自然能够借以此种方式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他自己说:“不肖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而著书。”(见《笠翁文集》卷二《曲部誓词》)而为了吸引更多的市民读者,以及优伶的传唱表演,李渔必须揣摩市场的需要,必须量体裁衣的创作出受欢迎的作品。这关系到他的生存大计。

因此李渔戏曲创作的目的性是很明确的,就是“娱人”。为了“娱人”,要让坊间书商看中他的戏曲作品,必须在可看性、娱乐性在加强。只有在这些方面着意加以揣摩,才可以获得读者、优人的认可。通过不断的实践,李渔的戏曲创作掌握了市场规律,也形成了对戏曲的更深一步的认识。
二、戏曲的题材选择及创作理念鲜明的表露了李渔戏曲创作的商业性。
李渔的戏曲创作,“十部传奇九相思”,多为风情喜剧。这样的题材风格,已然表明李渔的创作态度,他主要不是为自己创作的,而是要去愉悦大众。普通市民进入戏场,或者阅读文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买笑,为了度过空闲无聊的时间,增几许谈锋,减几分瞌睡。而一般观众最喜欢的便是男女爱情故事。
男女间的悲欢离合,最能感荡人心。而大团圆的结局,又往往能满足观众们的美好幻想,心灵得到愉悦。李渔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无论是《怜香伴》、《风筝误》还是《比目鱼》、《奈何天》,都透露出李渔鲜明的观众本位思想以及相关的服务供给意识。
在《闲情偶寄》中,李渔系统的阐释了自己的戏曲理论,其中不少就直接表明他的创作的商业性,比如论戏曲结构:作品无主脑,如散金碎玉,即令“观者寂然无声”,得不到应有的审美快感(《词曲部·结构第一·论主脑》);头绪繁多之作亦“令观场者如入山阴道中,人人应接不暇”;一线到底之作则“三尺童子观演此剧,皆能了了于心,便便于口”,“使观者各畅怀来”(《词曲部·结构第一·减头绪》)。
又如李渔论戏曲文体的浅显性,亦着眼于观众的特殊性:“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词曲部·词采·忌填塞》))。还有诸如“重机趣”、“意取尖新”、“缩长为短”等等理念都是以观众需要为理论依据。虽然是事后的理论总结,但也可看出李渔戏曲创作紧紧扣住观众,把握市场需要的特质。此外,为了照顾观众欣赏需要,李渔还专门对宾白、科诨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大多不脱离观众的好尚。着眼点正是在于此。
李渔名作《风筝误》尾声一曲写道:“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阙;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悲咽。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这可以看做是他的夫子自道。

显然,在李渔的观念中,以“钱”为中心,创作者与欣赏者相互勾连起来,观众和作家是一种商业卖卖似的关系。李渔的戏曲创作既然为观众的喜好所决定(背后乃是观众手中的钱),不得不努力去迎合他们的口味。比如戏曲为了吸引观众,常有一些秽笔科诨,李渔虽然反对这一做法,立主“戒亵”,但是却又指出说“谈事”之法:“说半句,留半句,或说一句,留一句,令人自思……借他事喻之,……则欲事未入耳中,实与听见无异。”(《词曲部·科诨第五·戒淫亵》)为了迎合观众的低俗口味而刻意揣摩,既避免了“亵”的恶名,又拥有其实,做出此种调整,则显然是一种媚俗思想。比之他所批评的“亵”,不过在五十步百步之间,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已。这足以说明李渔的戏曲创作主要是为了观众服务的,所以对于娱乐性、舞台表演性特加注意。
三、总结。
李渔的戏曲创作当然也有考虑到其他因素,比如讲求伦理观念的传达。但是探究其主要作品,却可以清晰地发现,他戏曲主要的创作目的就是“娱人”,就是“商业性”。就算是宣扬伦理,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市场性考虑。宣扬伦理成了当时通俗戏曲小说创作的套路,不但是作者,就是读者心理预期上也希望看到教化成分,假如没有这样的内容,读者就会不买账。因此我们在称扬李渔注重于戏曲特性的时候,不能忘了他的这种戏曲创作观以及创作成果,并不仅仅是出于艺术角度上的考虑,更多的是因为商业化潮流下的必然选择。